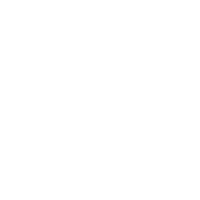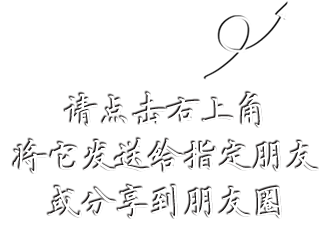故园菜花黄
桂林日报
2021年04月08日
马从春
又是一年春日归,风吹朵朵菜花黄。
这里的菜花,特指油菜花。尽管菜园里的青菜,它的花也是黄色的,几乎与油菜花一模一样,可是格局却大为不同。青菜是小家碧玉,娇滴滴的,人工精心侍弄养在肥沃的菜畦里,叶子铺展面积较大,花茎却长不高。油菜花则不同,随意撒播在大田大地里,层层叠叠,一大片一大片的,茎秆修长,花朵高昂,浓密而严实。
幼时,父亲把上十亩田地分为两份,一半种麦子,另一半种油菜。柔风轻吹,春天来临,田野里的油菜在春雨的滋润下,个头儿迅速长高,不消多久,便绽放出大块大块耀眼的金黄。放学回来,我喜欢爬上村口河边那棵老柳树,坐在青青的枝杈上看地上一望无际的菜花。那些菜花,万头攒动,似乎也在看我——柳树上一个顽童摇摇晃晃,轻折柳枝。柳笛声声中,嘹亮的春天,便倏忽间蹦出,氤氲弥漫在广袤的田地里。
我也喜欢抓菜花地里的蜜蜂和蝴蝶。有小伙伴告诉我,蜜蜂的肚里面有蜂蜜,只要抓住了,就能吃到。这个说法不时诱惑着贪吃的小小内心,以致于偷偷钻进菜地,糟蹋了无数菜花,也没能实现,最后被蜜蜂蜇疼了方休。蝴蝶也不是能轻易抓到的,而且我极怕它身上的粉状物,只得悻悻作罢。
母亲常常让我去菜地里拔猪草。下午放了学,我拿起蛇皮袋子,与小伙伴们一路打打闹闹,到田野里拔猪草。那时候种油菜,没什么化肥,大多是农家有机肥,也不兴农药除草剂,大片大片的青草长在菜地里,柔嫩嫩水灵灵的,仿佛绿色的地毯。
拔完猪草,天色尚早,我们便在菜地里嬉戏起来。捉迷藏,玩打仗,嘻嘻哈哈的叫声,弥漫在金黄的菜地。玩累了,躺在软绵绵的菜地里,身上浸满了青草的绿色汁液,脸上、头发上也都是黄澄澄的花粉。傍晚,扛着鼓胀胀的袋子满载而归,走进屋里,浑身都是菜花的清香。
菜花,朴实而单纯,是一种低调的平民之花。春日融融,李花桃花梨花等各色鲜花,高高在上,让你抬起头仰视,唯有菜花,田间地头,屋前房后,放低身子,矮矮地生长在那里,让你随处可见。你若不去观赏,它也不埋怨,兀自开着,照样儿蜂蝶自来。每一朵小小的菜花,心里都有着一个温暖而辽阔的春天。
菜花,还是一种会过日子的花。一朵菜花一滴油,在乡间,一个人踏着春日,静静地行走,走着走着,就会走到菜花深处。这时候,一种奇异的芬芳,会像蠕动的虫子,爬上你的身体,钻进你的鼻孔,沁入你的肺腑,即便回到城里,还会久久不散去。这是菜花的精魂,菜籽油的味道。
周末,回到乡下老家,青青故园,菜花金黄。老屋的四周,那些菜花或深或浅,明灿灿地摇曳在春日的阳光下。花开的时候,我如约回来,只是不知道,我认识的那些花儿,这么多年了,是否还记得那个曾经在菜花地里放牧旧时光的小小少年?
一地的菜花,一地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