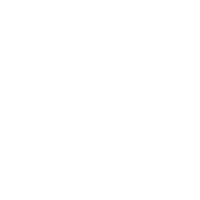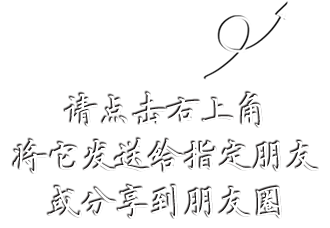永远的怀念
桂林晚报
2024年09月10日
■陈玉珍
他是我的初中班主任,姓苏。我们都喊他苏老师。
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彼时,他已经说不出话来,等我们和他做最后的告别。
说起来,我和他已经有20多年不见了。我上学那会,他还年轻,二十多岁的年龄,刚刚大学毕业的他,风华正茂,被分配到我们这所乡镇重点中学,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
彼时,我是语文科代表,他教我们数学——我最不擅长的学科。按理,我一个偏文科的女生,和他的交集应该不会很多。但他因为刚来的缘故,对每个同学几乎都充满了爱意——谁听课不认真了,成绩下降了,带的干粮不够吃了,他几乎没有不操心的。
他是那样蓬勃,充满了朝气。任谁看到他,都不免心生欢喜。
但喜欢这两个字,我却着实没有对他说出口过。
那时候,我们一个班有70多个人之多。以至于像我这样的书呆子,直到毕业,也没搞清楚有些人的名字。但他的记忆力却好到离谱,总能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刻,准确喊出每个人的名字。尤其是在晚自习的时候,他时常鬼魅一般出现在某一个窗口,然后,春雷炸响——被喊到名字的那个人,一准又被请到办公室“喝茶”去了。
像这样的待遇,我也曾有过一次的。
记得那是一个深秋的傍晚。吃完晚饭,我照例去校门外走走,却不想半道里被他请到办公室去了。他在桌前正襟危坐,眸色冰凉而又沉重。我站在他面前,像鹌鹑一样垂着头——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却莫名地心虚。
“你和大星怎么回事?”他威严的声音,像春雷一样炸响,“有人说,你们早恋了,是这样吗?”
……
我不记得自己当时说了什么,或者什么也没说。但我想,他一定记得当时我那双小鹿一样惊惧的眼睛——我疯了一样地跑出他的办公室,穿过校园里的杨树林,奔向校门外的田野,沿着长长的水渠,拼命跑下去……
那条路,仿佛没有尽头。我一个人蹲在枯黄的野草堆里,哭了很久,很久。
自那以后,我的成绩一落千丈。我不敢再去直视他的眼睛,尽管他一次次用充满了悲悯的眼光看向我,我却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有一扇门朝他永远地关闭了,发出咣当的声响。而那道水渠,也成了我唯一的避难所。不知道有多少个黄昏,我一个人在那里来回徘徊,或者呆立不动。失了魂。
年底的学校座谈会上,我作为学生代表,第一次给他打了差评。
直到有一天晚自习,下着大雨。眼看到了放学的时间,我却连个雨具都没有。他从我身后走过来,沉默地放下一件雨衣,又沉默地走开了。
我始终不肯抬眼去看他,直到脚步声在门外渐渐远去。眼泪才唰的一下,淌了下来。
自那之后,我在学业上渐渐恢复了起色,却还是避他如虎。直到中考以后,我毕业,远走他乡。我和我的苏老师,自此再也没有见过面。直到他出事。我扑在他的病床上,哭得不能自已,有愧疚,有委屈,也有这些年来,攒下的不甘和思念。
倘若他还活着,我一定毫不犹豫地扑进他的怀里,告诉他,当年那个倔强的小孩,长大以后,也成了另外一个他。呵护了许多小草,由着性子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