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芜:流浪文豪在桂林的五年 笔耕最勤奋的作家
桂林日报
2025年02月1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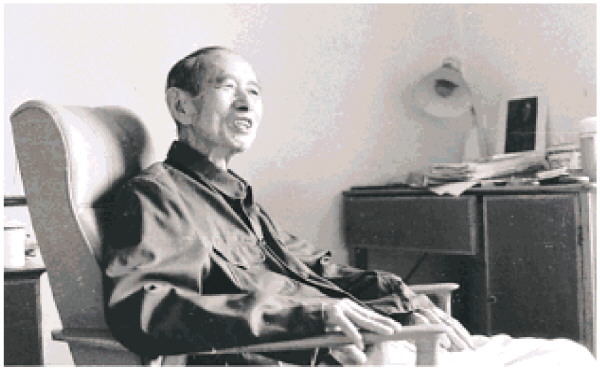
图①:艾芜(资料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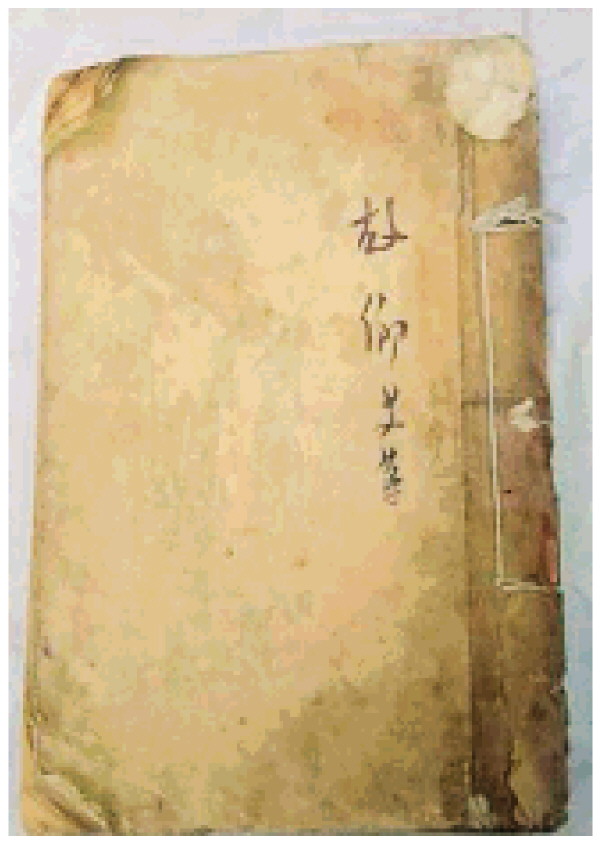
图②:长篇小说《故乡》在桂林时期所创作。 (资料图)
□本报记者 周文琼
艾芜(1904年—1992年),中国当代作家。又被人们称为南行作家、流浪文豪。艾芜一生追求光明,颠沛流离,受尽苦难。为了冲破封建主义的束缚,1925年夏天,他离开四川只身徒步南行。在长达6年的漂泊中,他到过云南、缅甸边境、新加坡等地。他经历万般磨难,产生过“自弃的念头”,但他还是鼓起了勇气,为了自己喜爱的文学而顽强地活下去。
艾芜回国以后,经济极端困窘,生活仍是不易。从1939年到1944年,艾芜在桂林5年。来时正是春节前夕,他带着家人甚至寻不到一处住处,而离开桂林时他坐着他称之为“世界上最糟糕”却又几经磨难才得到的光板车离开。在他凄苦的流浪岁月中,却始终坚持写作。他成为桂林抗战文化城时期笔耕最勤奋的作家。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荒地》《秋收》《黄昏》《冬夜》《爱》《萌芽》《逃荒》,长篇小说《山野》《故乡》……
流浪的旅途中在桂林的五年仍是流浪
“人应像一条河一样,流着,流着,不住地向前流着;像河一样,歌着,唱着,欢乐着,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艾芜去世时,这段话刻在他的墓碑之上,而这话也是艾芜人生的写照。
艾芜家境清贫。祖父种田,兼教私塾,父亲是乡村小学老师也是农民。艾芜小时候成绩好,小学还没毕业,便考上了成都联合中学,但因家境贫困交不起学费伙食费,他没能入学。
艾芜21岁时在成都的省立第一师范学习,由于不满学校旧教育和反抗封建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这是他流浪的开始。
南行路上他遭遇匪患,步行了两个多月,才到达云南昆明,在一家红十字会里当杂工。后又途经缅甸边境的克钦山,在一家马店做小伙计,晚上兼家庭教师。后又去仰光,因贫病交加,流落于街头,被汉人和尚万慧法师所救。病稍愈后,便替法师买菜做饭。在赴新加坡的途中,被人以疫检为名,强行扣留一星期。返回仰光后,又被逮捕,关进监牢,后辗转押解到香港,再驱逐到厦门。
艾芜回国以后,经济极端困窘,在友人的帮助下,靠着他人的募捐才得以勉强维持生活。
1933年3月。此时的艾芜已经加入“左联”。艾芜所在的部门是“大众文学委员会”。专门从事工人通讯员的工作;同时,还被安排到杨树浦工人子弟校义务教书。因联系工人通讯员,艾芜在上海被捕,后转到苏州高等法院第二监狱。经“左联”营救,鲁迅先生出诉讼费,由顶级律师史良(后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首任部长)出庭辩护,才得以释放。
1935年以漂泊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集《南行记》引起文坛瞩目。抗战爆发后,艾芜与其夫人王蕾嘉、长女珍妮先后从上海撤出,在湖南宁远团聚。1939年初,湖南战事危急,艾芜全家由宁远经山路到冷水滩,乘湘桂路火车于1月下旬抵达广西桂林。
艾芜一家是春节前夕到桂林的,那时的桂林一片紧张、混乱。幸好当艾芜全家徘徊在街头,无处投身之际,偶然碰上在救亡日报社工作的林林,才得以在太平路12号救亡日报社暂时安顿下来。后来举家数迁,到离城五里的观音山脚下,在临时搭起来的竹棚里定居,一住便五年有余。
当时的桂林城里,作家们过得艰辛是普遍现象,艾芜也不例外。战时稿酬极低,加上一些商人经常拖欠稿费,艾芜全凭一支笔养活一个五六口的家庭。他在《艾芜文集·序言》真实地袒露过当时的窘境:“在桂林,曾经短时间有过这样的事情,爱人生病,又没请人帮忙,便左手抱着小孩,右手执笔写文章。有好些作品写了就发表,没有好好加以修改。有的长篇,一面写,就一面发表。这都是不好的。但那生活的压力,确是叫人难以忍受。”艾芜一家甚至还被警察当作无业游民来看待。住观音山时,一次半夜,警察以搜查小偷为名,破门而入。他过着如难民一般困窘的生活。
桂林文化城时期笔耕最勤奋的作家
在《我与文学》一书中,艾芜曾说,在南行那最艰苦的岁月里。他也是“一路上带着书,带着纸笔,和一只用细麻索吊着颈子的墨水瓶。在小客店的灯下,树荫覆盖着的山坡上……把小纸本放在膝头,抒写些见闻和断想……墨水瓶和纸笔,从不曾离开过一天。即使替别人挑担子,我也要好好地把它放在主人的竹筐内的。”艾芜就像一位勤劳的农民,不分春夏秋冬,不管是严寒还是酷暑,他都在田野里耕作不止。
在桂林时,生活尽管艰难,据统计艾芜每月都要写五六万字的作品。艾芜的住处还能清晰地看见独秀峰,他写作的时候要不断抬头看对面独秀峰上挂着灯笼的标杆,如果标杆上只有一只灯笼,就表示没有敌机的迹象,他可以安心写作;如果有两只灯笼,就表示警报即将拉响,他要赶快收拾文稿,带着家人到旁边的山洞里躲起来。在郊外躲警报时,艾芜也是拿着“一把小得可怜的帆布小凳”,再以自己的膝盖为桌,坚持写作。
艾芜为中国现代文学留下了极具特色的一系列南行文学作品。在他创作的500多万字的作品中,《南行记》《南行记续篇》《南国之夜》《丰饶的原野》《故乡》等已经成为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不仅载入中国文学史册,还被翻译成日、俄、英、德、朝、匈、波等多种文字传播海外。
在桂林时期他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荒地》《秋收》《黄昏》《冬夜》《爱》《萌芽》《逃荒》,长篇小说《山野》《故乡》……
《南行记》是艾芜以第一人称手法描写早年南行生活的小说集,文笔非常细腻抒情。比如在其中一个短篇中,艾芜这么写:“昆明这都市,罩着淡黄的斜阳,伏在峰峦围绕的平原里,仿佛发着寂寞的微笑。从远山峰里下来的我,右手挟个小小的包袱,在淡黄光霭的向西街道上,茫然地踯躅。这时正是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残酷的异乡的秋天。”
在桂林时期的创作,艾芜的写作发生了转变。褪去了浪漫主义和传奇色彩,他此时的作品大多是现实主义,不在小说中抒情,而是冷静的叙述,一切让事实本身去说话。在桂林期间,他的作品有描写抗战的小说,有写大后方人民生活的小说,回忆南行经历和童年往事的小说等。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和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都在他的作品中呈现。艾芜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谈道,当时自己的创作是受“文艺为抗战服务”的思潮指导的。
而此时他的作品中也融入了很多地方元素。如长篇小说《山野》就是根据广西游击战争的事迹写成的。艾芜本人就说,《山野》反映的情况是有根据的。当时有打游击的人来同我谈过,广东有东江游击队……广西地方也有小股的抗日游击队。《山野》就是综合他们的战斗生活写出来的。
艾芜坚定的抗战决心和成熟的创作指导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也不是一蹴而就。艾芜少年时代就接受过“五四”反帝爱国新思想的洗礼,多年的漂泊生活更让他深刻体会被压迫下的劳动人民的疾苦,因为从事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他才被驱逐回国。回到上海后,“一·二八”事变所带来的屈辱,使艾芜将全部的创作热忱完全地倾注在反映人民抗战的题材上。逃难至湖南宁远生活的一年,他不仅接触了这个后方小城的各式各样的人物,了解他们战时的思想、生活及对战争的态度,还了解了大革命时期此地农民运动的史实,了解红军长征路过这里的遗迹。这些收获,都增进了艾芜对劳动人民的了解和对抗战的思考。
因此,到桂林后,在从事抗战文化活动的实际工作中,艾芜像所有进步文化人士一样,在党的影响和领导下,自觉地走出书斋,尽自己的全部力量,积极地投身到整个国家不可遏制的抗战洪流中去,显示出中国有识之士几千年来一直保持的“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优秀的爱国主义精神。
与在桂林的作家同舟共济
艾芜在桂林期间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以下简称文协桂林分会)领导核心之一,参与发起、组织文协桂林分会成立和该会在桂林的所有重大活动。还担任《抗战文艺》(桂版)编委,也担任过短期的副刊(《桂林晚报·独秀峰》)编辑。在桂林五年的工作和生活中,艾芜也与在桂林的作家团结协作、同舟共济。在与许多人互相认识、互相鼓舞、互相关怀的过程中,他不时地伸出他那双宽厚、亲切、无私的手,帮助了一个又一个的朋友、同志、学生……
1939年10月,文协桂林分会发起募捐援助贫病交迫的作家叶紫。11月,艾芜与夏衍等人发起援助叶紫遗族募捐,同年12月,他又与夏衍、周立波等15人联合发表了《为援助叶紫先生遗族募捐启事》。
作家王鲁彦在桂林的生活十分拮据,数种疾病的纠缠使他长期处于贫病折磨的境地之中。1943年6月,艾芜与王西彦多次商量如何帮助王鲁彦治病,他又多方奔走,于同月使王鲁彦主编的《文艺杂志》和三户图书社签订了出版合同。
1941年“皖南事变”后,已回新四军工作的吴奚如逃至桂林,找到当时在《力报》编副刊的聂绀弩。而后是艾芜找《救亡日报》的林林为吴奚如假造了一份证件,吴奚如才得以离开桂林到了重庆,后辗转到延安。
1944年6月,日寇逼近桂北,桂林危在旦夕。桂林大疏散,文化界人士又开始了新的、凄苦的逃难生活。艾芜和妻子带着四个孩子,坐上了他称之为“世界上最糟糕”却又几经磨难才得到的光板车,离开了客居五年的桂林。他们取道柳州、河池、独山、贵阳,于中秋节后到达战时陪都重庆,结束了三个多月的逃难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