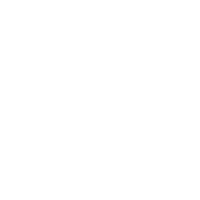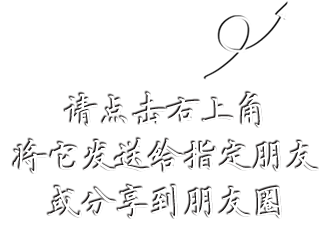母亲蔬菜
父亲瓜
桂林日报
2025年08月24日
□翟长付
小时候,我们家挨着生产队的猪场有块自留地。那儿的泥土总带着股猪场特有的味儿,逢着雨后天晴,泥土的腥气混着猪粪味,顺着风直往鼻子里钻。
父亲是生产队长,白天忙队里的活,夜里还得去猪场值夜班喂猪。为了给家里多挣口吃的,他把那块自留地拾掇得像模像样。种了冬瓜、南瓜、水瓜,还有一垄垄的香瓜,番茄架子也扎得整整齐齐。一放暑假,我和弟弟就盼着天快点黑,只要天一擦黑,就能跟着爸去自留地,吃上几口脆生生的水瓜、甜滋滋的香瓜解解馋。
母亲虽不像父亲那样整日泡在地里,但她自有一方“小天地”。在自留地的角落,母亲喜欢种开花的蔬菜。金灿灿的南瓜花,像一个个小喇叭挂在藤蔓上,清晨沾着露水,摘下来裹上面糊油炸,咬一口酥香四溢;紫色的茄子花星星点点,藏在宽大的叶片间,花落后结出的茄子,母亲会切成片,裹上蛋液煎得金黄;还有那白色的葫芦花,花瓣厚实,花蕊清甜,母亲常掐下刚绽放的花朵,洗净后和鸡蛋一起煮汤,汤鲜味美,连汤带花喝上一碗,浑身都舒坦。这些会开花的蔬菜,不仅装点了菜地,更成了餐桌上的美味。
猪场的房子是长长的水泥拱形,每到傍晚,父亲就挑几桶河水,“哗啦哗啦”往房顶上泼,给晒了一天的房顶降降温。完了铺上凉席,我和弟弟往席子上一躺,望着满天星星直眨巴眼;父亲就蹲在边上,吧嗒吧嗒抽着烟锅,给我们讲故事。
有天夜里,我眼瞅着自留地里有黑影一闪,急得直拽父亲的衣角说:“爸!有人偷瓜!”父亲吐了口烟,竖起食指抵在嘴边:“嘘——”我急得脸通红,说:“那咋不去抓他?”父亲往地上磕了磕烟锅,轻声说:“那是猪场后头的红林,爹妈走得早,跟着瘸腿的叔过日子,家里揭不开锅。我还寻思着摘几个瓜给他们送去呢。”我气鼓鼓地嘟囔:“偷东西就是不对!”父亲摸了摸我的头,说:“心里明白就行,就当没看见。他们爷俩能吃饱饭,比啥都强。做人啊,得有同情心,心要善。”说完,父亲故意大声咳嗽两声,接着又讲起了故事。
水瓜是菜瓜的一种,比普通菜瓜更粗壮,椭圆形的瓜身碧绿油亮,爬着几道浅绿色沟纹。为啥叫水瓜?咬一口就知道,汁水“噗”地溅一脸,又脆又甜,清清凉凉的,暑气一下就消了。我和弟弟最爱洗净了直接啃,“咔嚓咔嚓”,连皮带瓤吃得干干净净。
母亲也爱捯饬这水瓜。切成丝儿、片儿,拌上盐、糖、醋,再撒把蒜末,做成凉拌菜,就着稀饭能吃两大碗。吃不完的,就切成条儿,拿盐腌上,兑点苋菜糁老汤做成咸菜。这苋菜糁老汤可是老家腌菜的“魂儿”,用新鲜苋菜加盐捂出来的,酸香酸香的,腌出来的水瓜咸菜,放坛子里能存一冬,配着玉米糊糊,开胃得很。
每到夏天,我就馋这口家乡的水瓜。巧的是,岳母的菜园子里总种着一两畦。外孙和外孙女跟我小时候一个样,喜欢吃水瓜,天热了就扯着嗓子喊:“去太姥姥家吃瓜!”
这么多年过去,水瓜的香甜、母亲种的那些会开花的蔬菜,都还留在嘴里、刻在心里。就像母亲腌菜的手艺、父亲教我的道理,伴着瓜香与花香,成了我心头最浓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