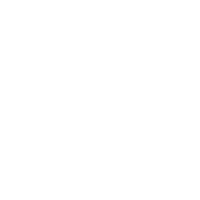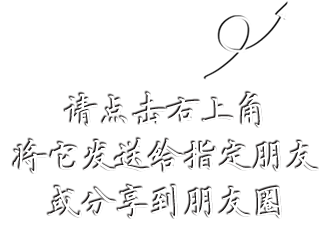酸坛记
桂林日报
2025年06月28日
□林仔
周末去逛早市,发现藠头的季节来了。一眼瞅见摊点上满满当当的白色藠头,想象着它们做成酸藠头的味道,我嘴里的唾液下意识地就开始分泌,这是我的味蕾记忆。我太喜欢母亲腌制的酸藠头了,在炎炎夏日来上几颗酸坛子里的藠头,真是一大乐事。
母亲爱吃酸,而且只吃自己腌的酸。从我记事起,家里就有大小不一、高高矮矮的酸坛子,这是母亲厨房里的宝贝。由于起的酸坛子多、用得多,好几个酸坛子原配的坛口片、坛盖都已经碎了,母亲拿家里不用的碗、酱碟取代,这也让我们家的酸坛子有了五彩的颜色,点亮了逼仄的厨房。小时候的我,喜欢蹲在母亲的酸坛子旁看坛沿里的水,坛盖边时不时会冒出一个气泡,仿佛呼吸一般,是有生命的。
每年进入初夏,母亲就开始起新坛。在市场上挑选合适的嫩藠头、仔姜、红辣椒回来,洗净后晒一天,待水分干爽又不至于干瘪时最好。在做食材准备工作的同时,母亲也要用沸水将老坛全部清洗烫过、晾干。待食材和坛子都准备完毕后,才开始做酸坛子。
母亲将水煮沸放凉,白开水里放适量盐和三花酒,然后将水倒入坛内,将晾晒好的藠头、子姜、红辣椒也投进去,坛子便有了第一缕魂。剩下的,就是静待自然的馈赠。
酸坛子是母亲的宝贝,虽然制作过程简单,但是酿的都是她爱吃之物,每一坛都不容有失,所以母亲从不肯让我插手。唯一愿意让我做的,就是交代我隔几日换一次坛沿水。待我灌满坛沿水,母亲还不放心,势必要跟上前来再确认一眼,看我是否偷懒、有没有灌满。
不过母亲对我的不信任并没有给我造成困扰,因为我也超级爱吃酸啊。看到母亲如此用心守护这几只酸坛子,想着在她的严格品控下,随后一年都会有好吃的腌酸,我就满心欢喜。每次蹲在坛子旁,嘴里的唾液就开始条件反射分泌,两眼放光,眼巴巴盯着不停地问母亲:“什么时候能吃啊?”
但是酸坛子是时间的馈赠,急不得。可小时候的我哪有这个耐性,最多也是再等半个月,就迫不及待催促母亲开坛尝鲜。母亲拗不过我,在我眼巴巴的期待中夹出了夏天的第一颗酸藠头。
酸藠头晶莹剔透,裹着酸水,一口咬下去能爆汁,清新的酸味顿时弥漫口腔,夏日的暑气仿佛在这一刻能被驱散。“成功!”我向母亲宣告酸坛子起坛成功。母亲看着我满足的样子也满眼笑意:“是不是啦?我也尝尝。”说完,母女俩各拿一双干爽的筷子蹲在酸坛子边,开始品尝起来,肩并肩、头碰头,那份共同的乐趣,是我和母亲心底最柔软的记忆。
酸坛子起好后,往后的日子,坛中物总会随节气流转:蒜苗、大蒜头、刀豆、豆角、萝卜……不同时节,母亲总会带回不同的食材,放入坛中腌制入味,像是把四季光景都酿成了琥珀。
我爱吃直接从酸坛子里夹出来的各种腌酸,也爱母亲根据时令用腌酸做的各种菜。
夏天,母亲会把酸藠头和酸辣椒切条,然后佐以牛肉一起爆炒。那香味,我放学回家一打开门就能闻到,开胃不已。
酸萝卜很快就能腌入味,必须尽快吃掉,否则能酸掉牙。为了消耗掉坛里的酸萝卜,母亲喜欢用肉末、魔芋豆腐拌上酸萝卜丁一块炒,酸味进入魔芋豆腐,拌在饭里可以连吃好几碗。
冬天,母亲喜欢用很多的酸辣椒、酸姜和酸豆角做佐料,与腊肉一起爆炒,腊肉的咸香被酸姜、酸辣椒、酸豆角的酸味调动,口感层次更为丰富,是冬日里全家都爱吃的下饭菜。
坛子里的酸水也不浪费。母亲用酸水调醋血、炒醋血鸭,再放入酸藠头,那鲜香,是我们家拿出来招待客人的“常胜将军”。
这么多年,我们的口味已被母亲的酸坛子“宠坏”。母亲的酸坛子不仅是她的宝贝,也早已成为家里的重要成员。四十多年来,我们历经了六次搬家,每次搬家,母亲都会把自己心爱的酸坛子细心打包、带到新住处、重新起坛。只有当母亲的酸坛子腌好、开坛,做出全家人熟悉的那道酸炒牛肉时,我们才会消弭掉对新环境的陌生感,真切感受到回家的感觉。那是妈妈的味道、家的味道。
是啊,坛中万物,早已随着时光流传,在光阴里酿成了家的味道,在一个个静水流深的日子更迭中,把人间烟火腌成了不会褪色的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