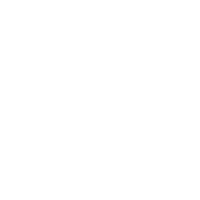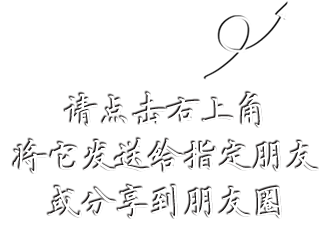葛麻藤跳绳
桂林日报
2025年06月01日
□张文燕
屋后山上的野藤开花了,一串一串紫色的小花,闪烁在密密匝匝的绿叶之中,在骄阳下特别显眼。小外甥问我:“舅妈,那是什么花呀?”我望向那些花和藤,回答他说:“那叫葛麻藤,我们小时候扯了来做跳绳的。”这句话说出来时,仿佛无意间按动了某处开关,无数熟悉的画面像放电影一般涌入到脑中来。
那座山叫猴子山,它如同一只巨大的石猴子脊背朝南端坐在那里。山下的学校叫黄坪小学,我的小学时光便是在那里度过的。
没有电视、电脑和手机的年代,我们的童年似乎有更多的游戏。一段小木桩,可以制成旋转的陀螺,用小鞭子抽着它转如飞轮;一捧小石子,可以磨成光滑的小圆粒,抛撒出一地欢声笑语;两根长竹竿,可以做成高跷,把自己垫高两尺……葛麻藤是猴子山专门赐给女孩子的礼物,我们手中挥舞的跳绳,几乎都来自它的馈赠。
跑过两道田埂,蹚过那条常常干涸的小河,就来到了猴子山脚下。一丛一丛的葛麻呈现在眼前,大大的叶片宽如手掌,筷头般粗细的藤茎柔软而坚韧。它们攀住周围的灌木、草丛,有时可以铺开到几米、几十米。听大人们说,这些野藤可是宝贝,它们秋天开花,结出来的果实可以做药,古时还用茎皮来做衣服。最有用的是它们藏在地下的根,又粗又壮,大的可以有胳膊粗细,可以当作粮食填饱肚子!
我们却只要它的藤!小小的人儿,顾不得带刺的灌木挂破衣服,刺痛手脚,只顾两眼放光地扯着这些野藤,比谁扯得更多,谁扯的更长更牢固。我们把扯出来的葛麻藤撸去叶子,它们就成了柔韧的绿色跳绳。现在想来这个过程比起如今到超市里买跳绳自然要艰辛些,可当年我们感受到的却只有快乐。
扯回来的葛麻藤,我们分成两类:短一些的叫小跳绳,只能留给各自单人跳;又长又粗壮的叫大跳绳,就可以用来给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集体跳啦。下课铃声是我们耳中最动听的音乐,它一响,我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跑出教室,到操场上挥舞我们的葛麻藤跳绳了。
那样的场景真是让人回味无穷啊!
内向的女孩子喜欢单独作战,选一个安静的角落,把手中的野藤舞得虎虎生风,脚尖随着绳子的节奏轻巧地跳动,马尾辫上下翻飞着,不时来点一跳两晃、交叉晃的炫技,有时候跳着跳着,还会叫唤着好朋友跑到跟前,单人跳就变成了双人跳。
喜欢集体跳的女孩子们,会召集起一群小伙伴,分配好两个人晃绳,跳绳运动就宣布开始了。当然啦,晃绳是轮流的,谁踩住了野藤中断了跳绳,她就成为下一个晃绳人。这样的集体跳绳可以不断有人加入,想跳的话,斜着跑进去,低头往浪起的绳子下一钻,跟上跳动的节奏就可以了。有时边跳边加人,会加到背贴背,脚踩脚,大家你推我搡,埋怨着谁谁谁踩到了自己脚,谁谁谁碰痛了自己的头,笑在一起,嚷在一起,直到有人一脚踏在了葛麻藤上,才喘着气停下来,争着指出踩绳的人,让她老实出去晃绳。
男孩子们也有自己的游戏,他们在进行一场陀螺比赛,比谁的陀螺转得快、转得久。他们埋头抽打着自己的陀螺,那陀螺疯狂地旋转,越转越快,越转越密,最后已经看不清陀螺的样貌,只见一圈白在土上疾速晃动,发出蜂鸣般“呜嗡、呜嗡”的声音。它可把握不住边界感,转着转着就往跳绳的人群中去了。它的主人自然知道侵犯地界的后果,可又不甘心让它停下来输了比赛,急得去拽晃动的葛麻藤,男女生大战由此爆发,跳绳与打陀螺都被迫中断了。
记得有一次,同族里的小表叔拽了我们的跳绳,还很得意地叫嚣:“你有本事去告诉老师呀!老师不是最看得起你吗?”我从屋檐脚下抓起一把“狗牙霜”——霜冻的一种,从后衣领塞进他的后背,恼羞成怒的他哇哇大哭了起来……
小外甥见我呆呆地只顾出神,问他的舅舅说:“舅,舅妈怎么啦?”我的先生回答说:“你刚才的问题触动舅妈的记忆开关啦,她一定是记起了小时候扯葛麻藤来跳绳的那些事,可比你们现在天天玩手机、玩电脑有趣多啦!”
那可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有记忆中的美妙童年,等到有一天他们长大了,在某个瞬间回首来时路,一定也是妙趣横生、令人沉迷的吧?还是普希金说得好: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