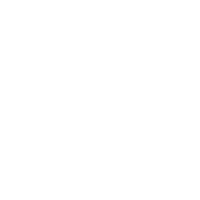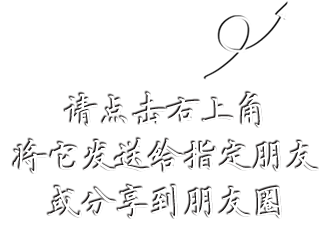粗羹淡饭
周身俱暖
桂林日报
2023年01月08日
□王太生
北宋太医孙昉,号“四休居士”,黄庭坚问他哪“四休”?孙答曰:“粗羹淡饭饱即休;补破遮寒暖即休;三平二满过即休;不贪不妒老即休。”老黄击节叹赏:“此安乐法也。”
那一句粗羹淡饭,显示普通人的平常心,喝五味调和的浓汤,吃淡饭,日子过得平稳妥实,简单饭食业已满足。
冬日里,一碗热气腾腾的疙瘩汤,养胃暖心。青菜,切成丁,在锅中翻炒,稍舀水,盖上木锅盖,待水翻滚,将事先调好的一碗面糊,用勺挑,一勺一勺,放入锅中,不大一会儿,一锅青菜疙瘩汤即已做成。那时深冬,天色向晚,外婆做好的疙瘩汤,锅中微凉。我盛一碗,放水辣椒等,呼啦呼啦地吃起来。吃青菜疙瘩汤时的最好境地,是在暮色四合,微雨清凉的傍晚。
同样是青菜,配上豆腐,便成一碗碧碧的热羹,有禾秆柴草的烟火气。青菜爽口,豆腐滑嫩,青青白白,好看好吃。大人们总是说,青菜豆腐保平安。不知道它们如何保平安,只知道那汤鲜,暖意融融,喝下直抵肠胃,奔五脏六腑去了。
粗羹在日常的餐桌,还有一碗丝瓜蚬子汤。有次采访,午餐时,有一碗丝瓜蚬子汤。蚬子与丝瓜合煮,虽是粗羹,却是妙物,青绿丝瓜切成细条,有韭菜的撮合,丝瓜、韭菜提香,再加上蚬子的鲜,惹得人要多喝几口。
《山家清供》里提到玉糁羹,当然也是粗羹。苏轼被流放海南时,生活清苦,和当地乡民一道以山芋充饥。儿子苏过想弄点好吃的给父亲改善伙食,没别的,就做芋羹。老苏吃得眉飞色舞,即兴赋诗:“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奶更全新。莫将南海金齑脍,轻比东坡玉糁羹。”
这样的食物,不只是古人吃过,我在多年前也吃过,用玉米糁搅成稀糊状,掺入煮得翻滚的粥中。一锅稠糯的小米粥,便有玉米的清香。
如果疙瘩汤、丝瓜蚬子汤、玉糁羹可称之为“粗羹”,则糊涂粥、粯子饭等是淡饭。
淡饭,亦粥亦饭,平平淡淡,简单、不讲究。郑板桥在写给其弟的家书中说,“暇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糊涂粥,以杂粮为主的早餐,做法简单,吃法随意。板桥先生手捧海碗,表情凝重,喝粥极有仪式感,神态近乎虔诚,两三口热乎下肚,浑身暖洋洋的。一碗糊涂粥,暖胃,又暖心。
他还在《赠白驹老友联》中坦陈好友,自喜“白菜青盐粯子饭;瓦壶天水菊花茶”。粯子饭是一碗淡饭。粯,是米屑。粯子,方言指粗麦粉。有人误将板桥先生的粯子饭认作“苋子饭”,是一个谬误。其实,苋子饭是苋菜汤浇拌而成的饭,米粒上一派胭脂红,粯子饭与苋子饭,并不是同一回事。从味觉上区别,粯子饭是淡饭,苋子饭是咸饭。
与粯子饭相对应的还有粯子粥。有饭必有粥,水放多了,文火煮,便成为粥。
我曾做过粯子粥。煮饭时先放水和米,略熟后,把调好的粯子粉倒入,搅拌,继续煮,至粯子散发出浓郁的麦香。煮好后的粯子粥呈红色或浅褐色,香气弥漫,喝一口,清爽柔滑。
那时冬天,我们经常吃山芋粥。粥汤清亮,却是微甜,里面有山芋的味道。山芋粥煮时,我喜欢听山芋块在粥中煮沸翻滚的声音,咕噜咕噜,锅盖边热气蒸腾,还没有吃山芋粥,手足之间便有了暖意。粥煮好了,盛到碗中,也不等凉上一会儿,便急不可待地吹气喝粥,一碗山芋下肚,暖意盈怀。
淡饭,朴素、亲切而归真,还原生活本来面目。
友人吴老三常在外面应酬,大鱼大肉吃腻了,回家喜吃一碗淡饭。吴老三以白开水泡饭,称之为“茶泡饭”,他把白开水当茶,让饭粒慢慢浸热、变软,然后以萝卜干佐餐,咬一口萝卜干,扒几口饭,将这一碗泡饭吃得风生水起。吴老三说,在饭店吃了一晚上,回家后觉得还是没吃饱。在他看来,在家安静地吃一碗泡饭,最是轻松自在,一碗泡饭吃得熨帖、舒坦。
唯有那粗羹与淡饭,才是寻常百姓的饭食,平淡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