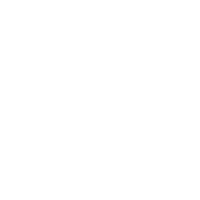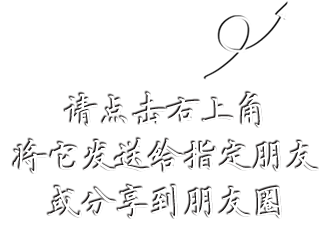秦牧与桂林
桂林日报
2022年06月23日

图①:年轻时的秦牧

图②:1944年,在桂林举办的“西南剧展”十人评剧团成员的合影

图③:秦牧夫妇(黄伟林供图)
□黄伟林
如今的中学生是否知道秦牧,不得而知。然而,上世纪60-80年代,秦牧却是当时中学生里无人不知的著名作家。那个年代的秦牧与杨朔、刘白羽齐名,被称为当代散文三大家。杨朔以诗的意境取胜,刘白羽以豪放风格著称,秦牧则以知识性和哲理性擅长。
知识性与哲理性的融合,有点接近杂文的品格。秦牧对此很有自知之明。他说:“我是从写杂文开始进入文学界的,当时所写的杂文,大抵登在《大公晚报》《广西日报》等报的副刊,以及一些文艺刊物上。后来,有相当一部分辑入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开明书店一九四七年的《秦牧杂文》中。由于我是从写杂文开始创作生涯的,以后我的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常常带些杂文风味。这是许多明眼的读者都能觉察到的。”
秦牧的创作生涯是从桂林启程的。1940年,秦牧进入失业状态。当时他的姐姐已经从广东到了广西,他决定到广西投奔姐姐。1941年6月,他到达桂林。最初,他在桂林兴安县一个叫做“39补充兵训练处”的军事机构当少校附员,相当于编制之外的工作人员,做的是修改文稿一类的工作,解决了吃饭问题。那段日子非常清闲,秦牧经常到灵渠洗澡。因为不适应军队生活,三个月后,秦牧到桂林另谋职业。
从1941年到1944年,秦牧在桂林工作生活了三年。桂林或许是秦牧人生中特别重要的一座城市。他是在桂林开始使用秦牧作为笔名,为桂林的《广西日报》《大公报》《力报》等报纸副刊以及《野草》《文艺生活》等文艺期刊撰稿。据秦牧自己说,秦牧这个笔名“隐约含有消除横暴之后,过和平生活的意思”。在桂林,秦牧不仅解决了就业问题,而且奠定了事业基础,甚至决定了他的思想走向。
在桂林的三年时间,秦牧写过一出多幕剧《风雨桂林城》、一篇长篇专论《易卜生研究》以及大量杂文,“这些杂文,初步显露了作者的创作才华和艺术个性,是秦牧正式登上现代文坛的标志。”
最初,秦牧到桂林是为人筹办《民众报》,但未办成。恰好钟敬文的夫人要去重庆,就把她在立达中学的职位让给了秦牧。秦牧成了教师。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桂林文化城进入高潮。如今的解放西路当时叫桂西路,书店云集,被称为书店街。夜晚,秦牧经常到桂西路看书。
秦牧在立达中学教了一年书后,中断了半年,专事写作,但没法维持生活,又到中山中学教书。根据《秦牧评传》,1943年,秦牧曾经邀请田汉到中山中学作关于抗战戏剧运动的报告。但学校教导主任从中阻挠,不准借用学校礼堂。秦牧只好把田汉请到他上课的教室里作报告。教室虽然小,但其他班级的同学闻风而至,教室内外,门口窗台,都坐满了人。秦牧在中山中学教书到1944年夏天。在立达中学和中山中学,他教的是高、初中语文,还担任班导师。
根据秦牧的回忆推算,秦牧在立达中学教书的时间应该是1941年9月到1942年7月,半年后,也就是1943年2月后,秦牧到中山中学教书,大约是教到1944年6月。
当时的中山中学是贵族中学,许多桂系军政要员的子女在这所学校上学,校长是唐现之。秦牧回忆,唐现之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副对联:“不敬师长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这副对联我曾经听朱袭文老先生跟我说过,如今在秦牧的回忆文章中得到证实。
多年后秦牧回忆:“这两年多的教书生涯,由于授课必须彻底弄清楚课文,才能够讲得清晰详尽。这个时期,我对于文学史、古文下了一番功夫,对于字词的析义,也逐渐掌握得比较精确细微。这对于我后来的文学生涯,很有好处。”
《秦牧杂文》中有一组作品,共七篇,皆以中外古代历史为题材,分别题为《囚秦记》《死海》《火种》《伯乐与马》《诗圣的晚餐》《罗马的奴隶》《拿破仑的石像》。这里我们介绍第一篇《囚秦记》。
《囚秦记》写的是秦始皇时期李斯与韩非的故事。
作品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写李斯的心理活动。这时候的李斯已经给秦王提交了《谏逐客书》,他的许多奏议也得到秦王的采纳,他对自己的前途也有了信心。但他耿耿于怀的是老同学韩非的状况,韩非正出使秦国,秦王读了韩非的《孤愤》《五蠹》等文章,颇有欣赏,李斯因此对老同学产生了忌恨之心。他面见秦王之时,说了不少韩非的坏话,甚至指使特工首领姚贾给韩非罗织罪名,以此为名建议秦王杀掉韩非。
第二部分主要写韩非的心理活动。这时候的韩非已经被李斯抓进了监狱,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李斯所为,他想起老师荀卿对人性的诅咒,对李斯充满了激愤之情。
第三部分写李斯与韩非的会面。韩非指责李斯的堕落,为了个人利益连自己的祖国都不顾,把秦国变成了一个大监狱,最后他重提他与李斯昔日的同学之情,希望李斯给他一个面见秦王的机会。李斯认为自己是为了秦国的前途和对秦王的忠诚,认为韩非不知天下大势,只是一个眼光如豆的书呆子,最后他把韩非作为韩国的奸细定罪,让韩非吞食毒药身亡。当秦王想起特赦韩非的时候,韩非的尸体已经僵硬了。
作品最后一段是这样一个场景:
就在这时候,远在南方的兰陵,八十高龄的荀卿,正弥留在人世,挣扎喘息于病榻上,他强睁开闪着浊水似的幽光的双眼,遥望远方,怀想他两个高足弟子,喃喃地正在呻吟祷告:“你们要好好地合作,天下的大任都在你们身上啊!这群悲惨的人民,这血污的中原……”
荀子是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但他的两个学生李斯和韩非却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这个作品涉及了荀子及其学生的两个关键理念:一是人性恶,二是法治。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李斯所代表的人性恶的一面,另一方面,也看到虽然李斯推行法治,但这个法治却与特务专政、虚构罪名和酷刑峻法联系在一起。
作品中的秦王也值得注意,对李斯的重用和对韩非的赏识,让后人看到这位君王确有过人之处。
《囚秦记》以生动的笔触写历史故事,与其说是杂文,不如说是小说,或者是一种小说体杂文。秦牧进入新中国时期后,作品基调多为对生活的讴歌,但《囚秦记》这个作品,却让我们看到另一个秦牧的存在。
作为文化城,桂林不仅是当时中国的文化生产基地,也是中国文化人脱颖而出的城市。秦牧不仅是在桂林开始文学创作的启程,而且是在桂林受到文坛注意。他曾经这样说过:
这时我不过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青年,虽然发表过许多文章,但连一本著作也没有出版过,在桂林文化界谈不上有什么地位。不过,读者和文学界也渐渐注意我了。有一个标志可以说明这一点,当一九四四年初,由田汉和欧阳予倩带头,以进步的剧团和戏剧工作者为骨干,联合其他的剧团,在桂林举办著名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时,演出了各种各样的戏剧,受到了各方的注意,重庆《新华日报》和桂林的许多报纸都发表了有关剧展的评论。当时参加演出的话剧有十六个。文协组织了一个“十人批评团”,对每一个话剧进行评论,文章由大家轮流执笔,这个团的成员有田汉、骆宾基、秦似、孟超、韩北屏等,我也被吸收参加了。这就是说,我渐渐地也成为当时桂林文化界的一员。后来我到其他城市去,报纸上居然也登载我的“行踪”消息了。
秦牧不仅是在桂林文化城成名,而且是在桂林文化城成婚。1942年,由翻译家何思贤介绍,他认识了当时《广西日报》的记者、编辑吴紫风。他们曾经一起看电影《浮生若梦》,并分别撰写了评论文章。结果吴紫风的影评获二等奖,秦牧的影评获三等奖。1943年,秦牧和吴紫风结了婚。
1944年5月19日,西南剧展结束,不久,桂林即进入风声鹤唳的状态。湘桂撤退是中国抗战历史上一幕惨剧。记录这幕惨剧的文字不算少。但不知为什么,了解这幕惨剧的人并不多。秦牧夫妇是湘桂撤退的亲历者,秦牧的回忆录对这段经历有较为详尽的记录,算是湘桂撤退一份宝贵的亲历记录。
6月27日,秦牧随中山中学搬到了阳朔。8月8日,衡阳沦陷,中山中学被迫解散,秦牧再次成为失业者。秦牧太太在融县一所中学任教,秦牧步行数百里去找太太。
9月8日,桂林第二次紧急疏散,融县也不安全了,秦牧夫妇变卖部分随身衣物,南下到柳城,准备乘车到贵阳。
柳州车站的火车上人塞得密密麻麻,水泄不通,想上车必须有人顶托从车窗进入,但顶托收费三千元。秦牧身材高大、年轻力壮,凭自身力量夫妇俩爬到了车顶。在车上两天时间,火车只走了一个站,秦牧夫妇身上旅费只够一个月,反复商量,最后决定下车步行。夫妇俩带着几十斤重的行李,沿着与铁路平行的公路前进,沿途看见无数死人,有一个人被火车压断了腿,痛苦不堪,向路人哀求,哪个有枪,给我补上一枪,结束我的痛苦。正好路过一个持枪人,朝他胸膛开了一枪,满足了他的要求。
从柳州一路走,经过宜山、怀远、德胜、金城江、河池、六甲等地区,由于原来基础差,遇上疏散人口密集,垃圾、尸体、粪便、腐物,到处都是,每座车站,都成了人间地狱,痢疾、伤寒、霍乱、疟疾等传染病流行,秦牧路过德胜车站的时候,正赶上霍乱流行,无人救治,无人收尸,十分恐怖。国民党军队不忘发国难财,用坦克做“黄鱼”买卖,秦牧看到军队的坦克上晾着小孩的尿布。秦牧夫妇一直步行数十天,终于到达广西和贵州交界的小镇六寨,遇到朋友,获得乘车的机会,乘车到达独山。这时已经是11月,听到桂林沦陷的消息。从独山乘车到达贵阳,又听到独山沦陷的消息。
秦牧很庆幸自己选择了步行,他后来听说他在中山中学的一个同事,小女儿夭折在火车上,连安葬的地方都没有,非常令人心酸。
从柳州步行到六寨,接近一千里的路程,走了数十天。一路上,秦牧亲历了广西西北部农民的贫穷和善良,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每晚投宿以后,我们借用他们的炊具做饭的时候,就有老人们天南地北地聊起来了。彼此有了感情,原本讲定要交宿费的,隔天早上他们又减收了。夜间,有时他们还来帮我们关窗户和盖被子,简直是深情款款,赛似亲人了。
我们经常自己烧晚饭,中午的一顿就在路边的小食摊上吃。广西的公路旁,凉亭里面,常有人在卖糯米粑粑,吃这种东西,是最经济不过的了。卖糯米粑粑的一般也都是农民,他们舀糯米粑粑给客人的时候,既想赚点钱,又怕给客人太少过意不去,好些小贩盛饭时,拿勺子的手竟颤抖着,看了令人感慨万千。
那些农民的贫穷令人难以置信。秦牧叙述了这样一件事:
我们在一户农家投宿,烧晚饭需要一点猪油,就向屋主要求转让一点,他从床底下抱出一个瓮子来,让我们从中舀取一汤匙。我一看,那猪油已经发黄了,颜色滋味都已经变了,尝一尝,有点呛喉。我问这油是什么时候熬制的,主人的回答使我不禁为之一怔。原来这是他在结婚时宰的一头猪留下来的,而在款待我们的时候,他的儿子已经六岁了!一头猪的猪油,竟一连六年都还没有吃完。
湘桂撤退给秦牧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也正是这次撤退,让秦牧和许多当时的文化人对当时的政府深深失望,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