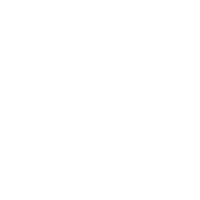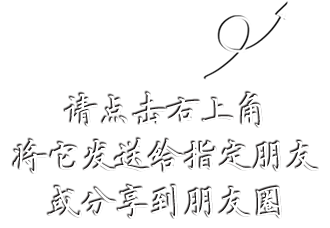故土暖冬
桂林晚报
2024年12月23日
■吴永谷
冬深正清冷,几场寒霜过后,把草木都囫囵个儿地遮了起来。唯小窗旁那枝红花,含苞待放,誓要把所有的寒冷与沉寂都点燃。这枝红花,已在书屋里静候十余个日夜,色彩依旧鲜艳。
或许并不是它足够顽强,而是那只父亲用故乡的泥土捏制的土陶花瓶,滋养了它。
想起小时候,每年冬天,父亲都会挖一些黄土。将其捣细、加水、搅拌,直到它们变得柔软而富有黏性。接着,将它们在砖头上细细糊抹平整,一个简易的土灶就诞生了。母亲点上柴火,烟囱里,袅袅炊烟升起,与冬日的寒风缠绵,淡淡的泥土芬芳氤氲在房间。一家人围坐在炉火旁,谈天说地。母亲不时起身,往炉里添上几根干柴,土灶上的大锅里,“咕咚咕咚”冒着热气,香气四溢。我和姐姐伸长脖子往里看,有时熬着一锅菜粥,有时是萝卜汤。虽不丰盛,但那时竟吃得异常开心满足。我们大快朵颐,暖流从舌尖滑入心底,直至全身都被幸福温暖。
如今想来,是故乡的黄土,陪伴我度过了无数个寒冷的冬日,无论岁月如何更迭,那份源自心底的温暖与满足,始终如初。
记得我去上大学前一晚,父亲塞给我一团东西,神秘地说:“丫头,到了外地,把它倒水里,沉一会儿,然后喝了,你就不会水土不服了。”我心想什么神丹妙药,当即打开纸团看了一下,竟是些泥土。父亲看我有些失望,又说:“这是灶底土,有妙用,你相信爸。”
到了学校,我将信将疑,还是按照父亲的说法喝了。后来在和故乡气候完全相反的城市,高强度的军训,也没让我感到不适应。不知道是不是那团故土发挥了作用。剩余的一点,我舍不得扔,仔细包好,放在床头。想家时,就拿出来嗅一下,闻着那熟悉的泥土香,故乡的一切又来到了身边,带着父母的叮咛,在耳边私语,给我鼓劲儿。
后来,我毕业后,又去了很多不同的城市。每次临行前,父亲照旧给我包一点灶底土,我问他:“爸,我都好多年没在老家生活了,喝这土,还有用?”他点点头:“不管去到哪里,它都管用!”我照旧收下。带上故土,心里总踏实些,觉得故乡的一切如影随形,伴随着我,继续向前。
去年回老家时,老来无事的父亲同别人学做陶器,挖的也是村里的黄土,我问他:“爸,这土黏度能够捏出东西?”他坚定地说:“这土啥都能做,放哪都合适。”果然,当得了灶上土,也能被父亲制成一个个形状各异的陶器。我回城时,行李多,就只带走一只花瓶。将它摆放在书屋里,插上各种花,每次走进去,总觉得自己不是拥有满屋的书,而是一屋子的花,而那些花开在故乡的大地上。
哪怕,岁末天寒,芳华迁徙,故土永远都是我的根,养育着我,滋养着我。不论身处怎样的冰天雪地,一想到故土,就能一瞬间荡起笑窝,溅起云霞,温暖着我度过一冬又一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