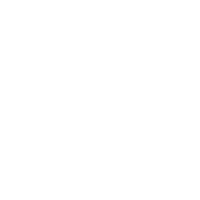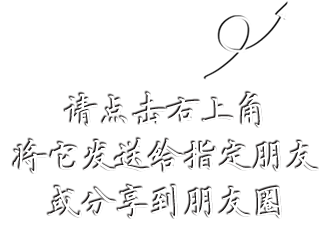我的入党三部曲
桂林日报
2025年06月29日
□诸葛保满
我的父亲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也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儿时,父亲常常给我描述他在上甘岭、雷州半岛等战场上那些党旗与军旗交辉的故事。我一边听故事一边抚摸着父亲胸膛上的党员徽章。那枚铜质徽章边缘刻着细密的齿轮,在煤油灯下泛着温润的光,上面还嵌着战场上的痕迹——父亲说那是上甘岭战役时弹片擦过的痕迹。这枚徽章引领着我从师范学校的课桌,到乡村学校的讲台,再到新闻夜班的灯光下,三次按下的红手印,盖在我向党组织靠拢的漫长信笺上。
1994年的春天,桂林市师范学校的迎春花爬满了礼堂的窗棂。作为一名师范生,我坐在团课教室的第三排,听老师讲党史。当老师讲到“李大钊在绞刑架下仍系紧领带”时,窗外的阳光突然斜切进来,照在他泛白的中山装上,那些褶皱里仿佛藏着无数个破晓的黎明。我顿时萌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团课结束后,我写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十个字,我在草稿纸上练了整整三晚,最后落笔时,墨水在纸页上洇出小小的花。
我递交申请书不久就师范毕业了。分配方案下来那天,我攥着报到证站在教学楼前,看见学弟学妹们正在擦拭走廊里的雷锋画像,画像边角被阳光晒得发脆。那时我满脑子都是“到基层去”的口号,却没读懂父亲那句“党员要先把脚跟扎进泥土里”的深意。留下未带走的申请书,我坐上了回乡的班车——回到家乡阳朔县葡萄镇周寨小学当乡村小学教师。
在乡村教学的八年时间,是我真正读懂“党徽重量”的开始。回乡教学的第八年,我在全镇教师基本功大赛上夺魁。领奖台的红布映着夕阳,当听到评委席有人轻声说“这么优秀,应该入党”时,我突然想起洪水中背学生过河的情景——那个扎羊角辫的女孩把湿透的作业本顶在头上,趴在我肩头说:“老师的背比爸爸的还暖和。”
那晚,我在备课笔记本上写第二次申请,窗外的梧桐叶落在窗台,像谁撒了一把碎银。粉笔灰沾在指尖,我忽然摸到纸页间夹着的半截粉笔——那是留守儿童小光用攒了一周的零花钱给我买的“教师节礼物”。这些沾着泥土气的温暖让我明白:父亲胸膛上的徽章从来不是军功章,而是他弯腰插秧时永远插在田垄最前头的那把标杆。
机缘巧合,我把第二份申请书交给党支部书记的第二天,调令就来了——我考进了县报社。站在人生的新起点,我用“先干好工作再想别的”来麻痹自己,又一次把申请书留在了学校。离校去报社那天,老校长把我送到校门口,拍拍我的肩说:“报社是党的喉舌,笔杆子要像教鞭一样直,可别忘了乡村教室里的晨光。”老校长的话像枚图钉,把“党媒喉舌”的使命钉在了我往后的笔尖上。
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刚转行成为新闻记者的我在隔离区采访时,曾见过护士长把党员徽章别在防护服外。她摘下手套的手布满勒痕,却坚持要对着镜头整理党员徽章:“戴着它,病人看见就有主心骨。”此后五年间,我在新闻一线见证了更多党员身影,直到2008年寒冬的冰冻灾害期间,除夕夜的山区,家家户户的鞭炮声次第响起,老电工打着手电检修线路,党员徽章在微光下一闪一闪,像他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党员就是照亮黑夜的那盏灯。”这些场景让我想起父亲讲的雷州半岛战役。他说,那时战士们用刺刀在钢盔内侧刻上党徽图案,月光漏进战壕时,党徽的轮廓就像田里永不倒伏的稻穗。
第三次写申请书时,我把父亲的蘸水钢笔灌满墨水,红格稿纸上的每一笔都像犁开黑土地的辙印。当笔尖划过“为人民服务”的词句时,窗外来了阵穿堂风,将案头的党章翻到那一页,而玻璃相框里的党员徽章正映着天光——徽章边缘的弹痕凹处,似乎还嵌着上甘岭的硝烟,又像凝着乡村稻田的露珠。我把它别在胸前,金属冰凉的触感贴着心脏,忽然明白了父亲对党的深情。这一次,经过培养和考察,我终于加入了党的大家庭。
如今,经过乡村教师、记者、编辑等职位历练,我走到了县融媒体中心总编辑的岗位。我常带着采编团队走村入户。在脱贫村的直播间里,我见过返乡党员用手机卖山货时把党员徽章别在直播架上;在防汛指挥部,我见过老党员用嘶哑的嗓子喊“我先上”时,党员徽章在汗水里发着烫。审校这些新闻时,我生命里的三份入党申请书总在提醒我:第一次申请是仰望火炬的光,第二次是懂得传递温度,第三次才明白——父亲的党员徽章之所以在岁月里包浆,是因为每一代党员都在用血肉给它淬火。就像此刻窗外的光,正透过办公室的玻璃,把案头那枚徽章照得锃亮。光斑在铜质徽章上流转,恍惚间能看见:上甘岭战壕里跳动的篝火映着弹片擦痕,乡村教室的木门窗里传出琅琅书声,脱贫村直播间的手机屏幕闪烁着点赞红心,防汛大堤上荧光马甲在雨幕中划出警戒线——而光斑的最深处,正映着我刚审校的新闻样稿,红笔圈注的“民生”二字之下,党员徽章的齿轮纹路里正奔腾着新时代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