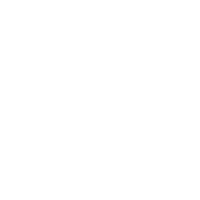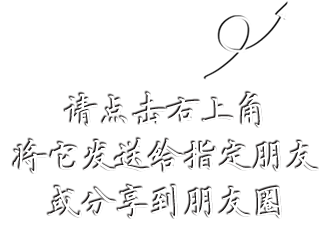墨香里的年
桂林日报
2025年01月18日
□张文燕
对联绝对是过年时的氛围担当。大街小巷里,对联一挂出来,不管长的短的、宽的窄的,纸质的绒布的,全国统一的艳红色,映衬出铺天盖地的喜庆,节日的气氛自然浓烈起来,闭着眼睛都能从红色的反光里感觉到“年”正奔跑而来。
我们家的对联是不兴上街买的,在娘家如此,嫁人后到了婆家也是如此。我的父亲和先生隔着二十多年的岁月,说法却如出一辙:当老师的人家,怎么能贴买来的对联呢?
小时候,家里的对联都由父亲来写。年三十的下午,年货已然备齐,年夜饭的各色菜肴在锅里蒸着煮着,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忙完了,父亲终于可以空出手来写对联啦。他耐心地用温水把毛笔泡上,再去裁纸。一张大红纸一般可以写两副对联,父亲把它分成四个长条,再按字数折叠成小的方块。为了写出来的字均称,通常还给每个小方块对角对折,相当于折出了“米”字折痕。砚台却是没有的,父亲喜欢拿一个小小的白瓷碗来代替。浓黑的墨汁倒入雪白的瓷碗里,黑与白互衬着,别有一番韵味。父亲用毛笔饱蘸了墨水,举在空中比画着。这个过程要花上十来分钟的时间,父亲仿佛在和字们商量,怎样的排列才更适宜更好看。一旦下笔,便是笔走龙蛇一气呵成。做过十多年民办教师的父亲写得一手好字,在附近村子小有名气。村里的红白喜事,只要他在场,写字之类的事基本交给他做。春联却是不帮别人写的,父亲有另外的事情要做。他把写好的对联一副副地摊在地板上,让它们自然风干。他自己则在满屋的墨香里,找来一个小锅,认真擦洗干净,开始自制贴春联的浆糊。以面粉为原料黏性已然很好,可父亲觉得还不够,他舀来一大勺糯米粉,在凉水里和均后才倒进锅里,文火慢煮,边煮边搅动。用这样做出来的浆糊贴对联粘得最牢,经年也不脱落。父亲把风干了墨迹的对联反过来,在背面均匀涂上浆糊,笑盈盈地说:“对联一贴就过年了,红红火火最喜庆了。”果然,红艳艳的对联贴上大门小门,映着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屋子,映着屋子中央一盆熊熊燃烧着的炭火,还有摆满桌面的菜肴,装满果篮的糖果。看着这一切,谁的眼里心里能不被“年”给填满呢?
我考入师范后的第一个寒假,父亲把手中的毛笔交给了我。他帮裁好了纸,甚至帮折叠好书写的印痕,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那样的场景让人紧张不已,我握着毛笔,在空中比画了半天都没敢下手。父亲说:“写吧,写字不怕丑,只要笔笔有,写多了就好看了。”在学校里,书法这门课我可从不敢懈怠,不但课上得认真,课后还很勤奋地每天练习,自认为落在书法纸上的字还将就能看,谁知落到这红彤彤的对联纸上简直就丑不堪言了。大冬天里,写完两副对联让我出了一身的汗,最后贴上大门的对联让我惭愧得不愿承认是自己写的。父亲倒是乐呵呵地逢人就说:“今年的对联换人写了哦!”博得人家不知是真心还是敷衍地夸一句:“你家出了个女秀才哩!”
结婚以后,我的先生是书法爱好者,临摹过一些诸如赵孟頫、文徵明等大家的字,写起来行笔很是流畅,写出来的字也有些大家风范。他不但给自己家写,也给亲戚朋友们代写。临近过年,客厅中每日里都摆满了需要晾干墨迹的对联,有时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对联的用纸从父亲那个年代的统一裁纸,换成了各式专用的对联纸,长的短的,宽的窄的,纯色的带花的,应有尽有。也不再需要人为地折出“米”字格,纸上早用漂亮的圆形图案规划好了。不变的是满地抢眼的红,逼得人眼睛都睁不开。你可以闭上眼睛默默地享受着满屋的墨香,让心融化在梦幻般的诗情画意里。家里人常开玩笑说,干脆到街上摆摊帮人写,看人家一个年过下来,可以收入大几千呢!先生笑嘻嘻地说着“我看行”,却从来没有付诸行动,他的对联从来都是免费的,他喜欢的应该也是那样一种氛围吧:年前的几天里,来拿对联的人络绎不绝,他们脸上含着笑,嘴里说着感谢,有时还会硬塞过一个“利市”,主宾间便推让了起来,你来我往的好不热闹。“年”在这个时候悄悄地溜了进来,阳光般地洒满了屋里的每一个角落。
家家户户贴上了对联,鞭炮就次第响起来了。鞭炮的红映着对联的红,上上下下红成一片。都说中国红有着神奇的魅力,代表着热烈、喜庆和吉祥。我们用笔蘸上浓浓的墨汁,让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在这耀眼的红色中流淌,我们的“年”就有了颜色,有了底蕴。平凡如你我,就这样成为岁月长河中小小的一滴水,在不知不觉中向前奔腾,继往,也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