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骏马,自由驰骋在文学的旷野
□本报记者 韦莎妮娜
桂林日报
2024年08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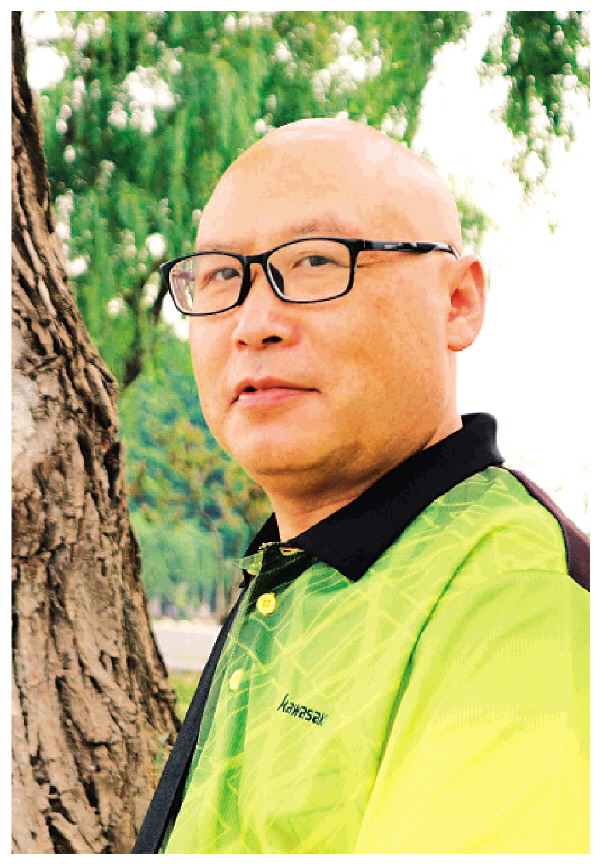
◥作家光盘

◤诗人黄芳
7月31日,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名单出炉。我市作家光盘(瑶族)凭借长篇小说《烟雨漫漓江》获长篇小说奖、诗人黄芳(壮族)凭诗歌集《落下来》获诗歌奖。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是由中国作家协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主办的国家级文学奖,与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儿童文学奖分量相当。骏马奖设长篇小说奖、中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诗歌奖、散文奖、翻译奖,每个奖项获奖作品不超过5部。自1981年颁发以来,整整13届,历时43年,只有4个桂林作家获此殊荣。上一次桂林作家获奖还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
两位获奖者在当代小说和诗歌领域耕耘数十年,早已成名。与文学为伴的半生,他们像一个忠实的观察者,描摹芸芸众生世间百态;又像一个高超的捕手,精准地捕捉到藏在人性最细微之处的幽暗和闪亮。文学如一苇,借助它,他们穿越人生的伏流,抵达了更辽阔的彼岸。
作家光盘:抓住那条灵感的“金丝线”
踏上文学之路是时代的必然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无数文艺青年至今还会集体怀念的黄金岁月。遍地开花的文学社、文学期刊,安放着文艺青年们高涨的热情。金庸、三毛、琼瑶、王朔、汪国真、舒婷、北岛,更是顶流一般的存在。朋友见面言必谈文学,人人都揣着文学梦、作家梦,就连征婚启事也要将“爱好文学”写进去才能获得青睐。
在狂热的文学年代,很难做个局外人。光盘就是当年庞大的文艺青年群体中的一员。
生于1964年,他的青春期恰好与八十年代空前的文学热交叠。文学书籍、杂志报纸、写作阅读渐渐成为光盘一生所爱。十八岁那年,光盘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散文,紧接着是小说处女作。因为时隔太久,他现在怎么都回忆不起来文章的标题。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从稿纸到铅字,大大激励了青年光盘。他或许没有想到,和文字的半生缘将就此开启。
于作家而言,对文字的驾驭能力是随年岁增长与日俱增的。生活吃得越透彻,笔下的文字就越张弛有度。但青年作家没办法一下就拥有很丰富的生活体验,于是阅读就成为了他们拓宽阅历的捷径。光盘说,在自己的文学之路上受到了很多名家的影响,比如鲁迅、汪曾祺、沈从文,国外的川端康成、夏目漱石、马尔克斯、福克纳、卡夫卡等,还有本土作家如毛荣生、鬼子,他们都给了自己文学的养分和力量。
1987年,光盘被分配到了桂林水泵厂工作,在国企工作的那几年,他坦言“丰富了自己的人生”。也正是这段经历,让他对国企有了一定的了解,为日后小说创作积累了素材。
1993年,光盘考进了漓江日报,后调入桂林日报社做副刊的编辑和主任。光盘说,自己从未把作家当作专职,“生活第一,工作第二,写作第三。对于作家,经历越丰富越复杂越好,它会成为创作的富矿。”
但因为种种原因,光盘的创作停顿了数年,直到新千年来临,他才重新拾起笔和纸写作。
人与自然的秘密,藏在生生不息的江河中
光盘是桂林人,同时也是少数民族。很多年前,他就想为漓江写一部小说,却因为太过于熟悉,迟迟下不了笔。
2022年初,光盘突然有了灵感,似乎找到了那条串起这部小说的“金丝线”。他立即动身前往漓江上游采风。
漓江上游水源清澈,小溪纵横,散落在大山褶皱里的村舍既独立又相互关联。光盘在采风中注意到,无论是哪座村庄的村民,无论哪个民族,大家都很淳朴,也很崇敬自然,绝大多数人都懂得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法则,也知道人与人和谐共处的可贵。
也正是同一年,光盘看到中国作家协会发布的2022年度定点深入生活项目申报通知。“这不正是一个好机会吗?”光盘试着填好了申报表格,没想到竟通过了专家层层论证审核。
光盘意外又惊喜,写作时间很是紧迫。但为作而作,是不会有精彩的故事的。光盘跑到漓江上游兴安县华江瑶族乡桐子坪,呼吸新鲜空气,跟村民喝油茶,喝土酒,从村里的家长里短聊到年轻人的爱情观,许多故事就像溪水自然而然流淌出来。
在光盘这本《烟雨漫漓江》小说中,有明灯、明山两位巡山工,他们的原型就是漓江源头猫儿山管理站的员工。猫儿山自然保护区是漓江源头核心区,原始森林厚实宽阔,珍稀的动植物多,因此常常遭到偷猎偷伐。
在收集故事的过程中,光盘深切地体会到了巡山工的不易。“每个站管理超一万平方米,林子厚,峡谷多,河流多,每天必须巡山到边界。除跟偷盗者斗智斗勇,还要时时提防攻击性强的野生动物。他们每天都处在危险之中。因为长年巡山,每个人的皮肤都显得比同龄人的要黑。他们的工资也不高,也难得与家人团聚。”光盘说,有一个名叫侯远杰的年轻人让他印象深刻。侯远杰曾去外地打工,因为要照顾父母回乡,到自然保护区工作后,满以为就地就业可以一举两得,哪晓得既照顾不了父母,也没有理想的收入。但一年巡山下来,他与山里动物、植物、泉水、小溪、河流打交道后,深深爱上了这个工作。女朋友因为他的固执,和他分了手,如今大龄了他还是单身一人。“不过他说一点不后悔,猫儿山的一切就是他的恋人。”
“严冬过去,春天到来,漓江边的故事正在发生。人与自然的秘密,隐藏在生生不息的江河中……”翻开光盘的《烟雨漫漓江》,一群有血有肉,各有性格的角色跳入眼帘。在明灯、明山、明灯妈、九桑、晓巷等人物群像身上,漓江儿女淳朴善良、有情有义的美好品质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小说中,光盘还思索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并且提出了纯净和谐的社会生态理想。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东西这样评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漓江。作家光盘用小说家的角度,讲述了漓江沿岸人与自然的故事,原来平凡的日子里还有那么多动人的篇章。”
2024年7月31日,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名单出炉。光盘的长篇小说《烟雨漫漓江》获长篇小说奖。
“在漓江之源,我看到枯枝败叶之上晶莹的一摊摊浅水,它们安静地躺着、浮着,在鸟虫鸣叫声中、在浓荫之下,安详地享受大山的灵气。再往前走,我听见汩汩水流声,听见哗啦啦的流水声,看到了微型瀑布。你很难不被如此纯洁之水打动。一江碧波,永葆清流,就是大自然对有心保护它的人最好的回报。”
那根“金丝线”,随着漓江起伏的波涛,回到了光盘手里。
别停下对人生要义探寻的脚步
2003年,光盘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笔耕不辍的他,在这些年写出了40余万字的中短篇小说、散文。长篇小说《摸摸我吧》《请你枪毙我》《王痞子的欲望》在业内有一定影响力,其中《王痞子的欲望》斩获广西文艺创作最高奖“铜鼓奖”。由于小说风格犀利,光盘和田耳、朱山坡还被专家们冠以“广西后三剑客”的称号。
“读光盘的小说,常常无需考究他笔下荒诞故事的可能性。他并非故弄玄虚,他只是始终对人性在进行探秘与拷问。”一位文学评论家如是说。
“写作是‘千古事’,急不来。写作的目标不是冲奖,而是释放内心的情感,探寻人生、人类的要义。”光盘说,从拿起笔写作,到担任桂林市作协主席,二十多年来,他把自己从一个青年写成了“准老头”。在与青年作家深度交流时,他也会说出自己的写作观,那就是要深入生活、思考生活,先把每一篇作品写好了,奖是水到渠成的事。
在光盘2018年以前的文学创作中,“沱巴镇”“玫瑰镇”“桂城”是频频出现的文学原乡。“沱巴镇”是他的瑶族乡村,“玫瑰镇”是娇媚的乡野,“桂城”是喧嚣的桂林城。2018年后,光盘把创作的重心转向了本土,长篇小说《失散》写的是湘江战役之后失散红军的命运遭际和他们不屈不挠的无畏精神。长篇小说《烟雨漫漓江》同样是本土题材。“目前我完成了一个长篇小说和三四个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写的是发生在桂林抗战时期的故事,具体来说就是以飞虎队03号油库被日本飞机轰炸、中共地下党与国民党联手寻找日本间谍为主线,揭露鬼子的凶残、狡猾,颂扬中国人的英勇、众志成城。”
用脚去丈量大地,写出那股紧抓大地的人间烟火气。走到六十岁的门口,光盘手中的笔还要继续写下去。
诗人黄芳:我观察庸常生活下的炽热暗流
拥有平衡术的幸运儿
和黄芳的相识是在十多年前的一场诗会上。在喧嚣声中,黄芳保持着特定的说话节奏和音量,轻柔、缓慢,头上永远戴着贝雷帽,就像一种对世界温柔又坚定的宣告。
大家漫无边际地聊天。一个小细节让我记住了这位特别的女诗人。
黄芳的文学摇篮是一个小小的天井。小时候因为社恐,黄芳害怕跟家里人以外的任何人打交道。逢年过节是她最头疼的,因为不懂怎么问候和寒暄。还好开明的母亲从来不勉强,在外面总是护着孩子。
在一本书的后记中,黄芳回忆说:“母亲在外替我挡了回去:没事,虾蟹各有各路。”文学就是她的路。早慧的黄芳很小就意识到,文字是有魔力的,哪怕是一张说明书,她也能津津有味地看半天。一方天井,是儿时黄芳的“理想国”。在这里她不必想破脑袋开口寒暄,她可以阅读喜欢的书籍,还可以无所顾忌地和掠过天空的鸟儿对话。
学生时代的数理化、步入社会后的人情世故,都不在黄芳擅长范围内。但只要回到文学的舒适区,黄芳是那样的游刃有余,又是那样的自信。16岁,黄芳发表处女作,编辑有些惊讶——如此老练的行文和表达超越了她的年龄。
父亲是黄芳文学路上一个很重要的启蒙者。黄芳说,父亲是一名民间壮剧作家,一辈子用土壮话写了60多部剧本。小时候,她特别喜欢坐在父亲身边,看父亲飞快地写字,那些散落在泛黄时光里的稿子,也不知不觉滑进了她心中。
记者、编辑、教师,黄芳很庆幸自己从事的绝大部分职业都跟文字相关:“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在梦想与生存中拥有平衡术的幸运儿。”
诗人属风
如果说人有属性,黄芳应该属风。
“写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写作。”在创作与生活互为镜像的30多年中,黄芳从一个“笨拙胆怯的女孩”,成长为一个母亲、一个灵性的书写者。
“简单庸常的生活底下是炽热的暗涌。像一张神秘的网,筛掉什么,留下什么,批判什么,铭记什么,它们非常清楚。”黄芳始终保持着像风一样入世又出尘的态度,默默观察生活中细微又打动人心的东西。
在她的诗歌中,一切回到了日常生活中来,一切回到了个人中来——黄昏时低飞的鸟雀、屋后的柠檬树、父亲伏在小书桌上埋头写作的样子、母亲一遍遍清扫的庭院、那片绽开了蓝紫花瓣的苜蓿、被忽略过的春天、河流……黄芳的笔下,涌动着真诚又悲悯的情怀。“所有在画面与扩音器里重复过的人与事/要无限缩小,隐入低处/被忽略过的春天、河流/要沿着那条蚂蚁经过的路,一一返回/从今天开始,我的身心要紧贴荒野里小小的草/它们没有名字,但一出现就得到了我的深爱。”(《卑微》)。
“‘我要为自己买些花’/穿过伦敦第十大街/有一家花店/不一定都是玫瑰,但要有几朵/尚未盛开/一定要在清晨,用旧报纸包起/咔嚓咔嚓跑过积雪/咔嚓咔嚓/你在打字机上敲下属于自己的房间/敲下玻璃,窗棂,以及栅栏/你耽于幻想/用文字试探命运的深浅……”(《咔嚓咔嚓:致弗吉尼亚·伍尔夫》)。
有人评价黄芳的诗歌“一直很安静,一直很灿烂”“有生命的温暖”,黄芳则说自己是“一个很容易有幸福感的人”,慈爱敦厚的父亲和开明包容的母亲给她创造了自由的成长环境。生命的暖色基调始终如一件柔软温暖的盔甲保护着她,任凭世界投射出尖锐的箭,黄芳都能温柔地面对,不疾不徐地躲开。
安稳地落下来
命运总是喜欢躲在角落,冷不丁地给出一记伏击。2020年,黄芳的“平衡术”魔法被疫情击败。母亲的三度入院,焦头烂额的工作,不由分说地将黄芳推上了高速运转的轨道。
在母亲生命倒计时之际,她仍在见缝插针地看稿,未能好好地、郑重地与母亲告别。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黄芳困于幽暗的钝痛中无法自拔。
母亲最后的话是“凡事有得有失”。这也成为了黄芳重新找回人生平衡的密钥。她鼓起勇气,换了一份工作,过筛掉与人生内核无关的边角料,一点点地拿回了自己的节奏。“岁月趋变中,她已修剪掉多余的枝蔓,而童年对万物的情感态度、内在的骨头始终在。它安稳地落在无数的黄昏、风、鸟雀以及木叶中,落在梦想与现实的陈述与隐喻中……”黄芳如是写道。
2022年,黄芳被评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同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她的诗集《落下来》便是其中之一。2024年7月31日,黄芳凭借《落下来》斩获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诗歌奖。
在这本诗集中,黄芳给予了微小的事物以足够的关注,寻找生命的重量、时间的痕迹,描摹壮乡独特的山川河流和花草树木。“她总是能在细节和幽微中激活出想象的闪电与低沉的雷鸣,能够在司空见惯的表象背后上演戏剧化的灵魂舞蹈。”诗评家、《诗刊》副主编、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委霍俊明说。
作为一名女性少数民族诗人,黄芳以女性的角色和视角进行情绪体验,捕捉到了最细腻、幽微的情感起伏,她在书写时把女性身份带入、投射、共鸣。“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一生都是在准备、创作、修改自画像,由此诗歌分担了自白、祷辞、安慰剂和白日梦的功能。她们(黄芳等女性诗人)通过理解、扮演、重组、建构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形象来抵达‘永恒的女性’。在诗人与自我、事物、空间、元素的对话、磋商、盘诘中,我们看到,一个女性在不断地回望、面对、直视、打量、凝视中,过去时的我、此刻的我以及未来的我相互交织、彼此探寻。”(霍俊明语)。
“三十年来/我在尘世中奔走/或轻或重的风,吹过/绿的山峦黄的木叶,吹过我”……走在风里的黄芳,随命运高低起伏。她暗暗攥紧了拳,一个漂亮的旋转,稳稳地在中年落了下来。

